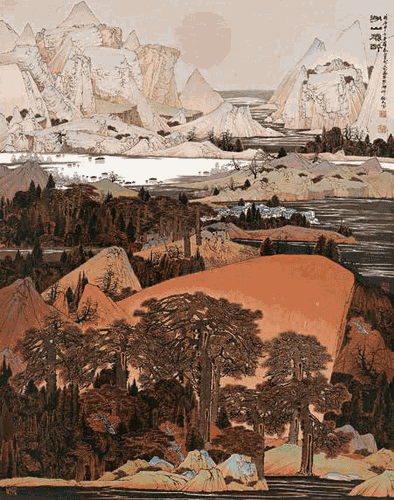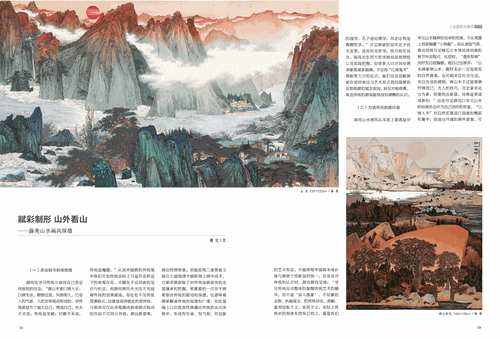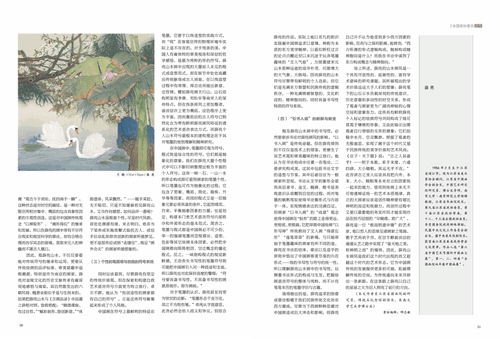首頁>書畫>畫界雜志>2022年第二期
賦彩制形 山外看山—薛亮山水畫風探微
(一)承古創今的傳統觀
薛亮在學習傳統方面有自己堅定而獨到的信念:“畫山水要以情入手,以情生法,順情達意。風格即人,它是人的氣息、人的世界觀而形成的。學傳統就是為了強大自己,塑造自己。對天才來說,傳統是圣殿;對庸才來說,傳統是魔窟。”從其中國畫的傳統觀中我們可知傳統實際上只是歷史積淀下的客觀存在,關鍵在于應用者的覺識與機變,而薛亮畫風中無處不充溢著傳統的因果源流,卻處處不見傳統因襲程式。這就是深而能化的真傳統,與那些僅僅玩弄筆墨或拼湊圖式構成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語。畫出新意難,畫出性情更難,若能實現二者兼備又暗合大道規律才能稱得上畫中高手。它要求畫家除了對傳統繪畫語言的全面繼承和把握,更重要的一點在于畫家取法傳統的路徑和深度,也意味著畫家解讀傳統的高度和廣度。在此基礎上以自我真性情灌注傳統的法式體格中,形成有生命、有氣息、有血脈的藝術形態,方能體現中國畫本體價值與畫家個性彰顯的統一。在談及對傳統的認識時,薛亮頗有見地:“學習傳統應當整體的掌握傳統藝術的精華,而不是‘盲人摸象’,不知象的全貌,執偏蓋全,把傳統異化、曲解,濫用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實際上傳統中的很多東西早已有之,看看我們的國學,孔子是倫理學,而老莊則是模糊哲學。”可見畫家的層次在于有無思想,進而有無哲學,技巧則在其次。薛亮對東西方哲學都有深刻領悟以及實踐把握,但很多人只對其繪畫表象做諸多揣測,才會有“江南鬼才”等貽笑大方的論點,他們往往忽略畫家在語言表達與藝術形式背后隱匿的思想根源和觀念取向,甚至對他倚重、取舍傳統的源流脈絡沒有清醒的認識。
山-水-295×535cm--薛-亮
(二)力追宋元的踐行者
薛亮山水畫風從本質上看就是對宋元山水精神的沿承和發展,不從筆墨上刻意精雕“小情趣”,卻從畫面氣質、章法結體乃至樹石云水等具體而微的細節中變程式、化結構,“遺形取神”而抒發自我胸臆,他自己也曾言:“山水畫家畫山水,題材未必一定是現實的自然景觀,也可能來自社會生活,來自生活的感悟,畫山水不過是借景抒情而已。古人的技巧,完全拿來化古為新,但要找出新意,經典是常讀常新的。”由此可見薛亮以宋元山水的經典形態作為自己創作的筑基,“以情入手”對自然實景進行高度的概括和集中,創造出開闊的畫外意象,可謂“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這種狀態是對時空的凝結,是一種對無限世界相對集中、概括的包含具象性因素的主觀性創造,這是對中國畫傳統觀念“以神取形”、“離形得似”的繼承和發展。所以在薛亮的畫中常有不盡符合現實和視覺科學的章法,卻有合情合理而各盡其態的意境,直取宋元人的神髓而不落古人窠臼。
因此,觀薛亮山水,不僅僅要看他對傳統符號的繼承和運用,更要從傳統繪畫的品評標準、審美意趣中追根溯源。特別是作為南京的畫家,薛亮對金陵文化的歷史文脈傳承有著深刻地感悟與淘染,其自然散發出的六朝風骨、魏晉余韻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如果把薛亮山水與《古畫品錄》中品藻之辭相對照,皆極相配:“精微謹細,有過往哲。”“賦彩制形,皆創新意。”“體韻遒舉,風采飄然。”……隨手采拾,無不貼切。只是不知謝赫若見薛亮山水,又當作何感想,如何品評一番呢?薛亮山水雖極富個性,盡顯時代風韻,卻處處淵源有緒、來去明白,絕非當下某些或東施效顰式臨撫古人、或信手狂涂亂抹即言創新的畫家所能夢見,更不是那些總試圖“走捷徑”、做足“畫外功夫”的畫家所能想象的。
湖山秋色-144×184cm--薛-亮
(三)個性的筆墨觀與自我的符號系統
同時應該看到,盡管薛亮有堅定的傳統價值觀,但在探索和構建自我藝術語言符號方面更為特立獨行、卓爾不群,他認為“有創造性的畫家都有自己的符號”,正是這些符號聚集起來形成了個人風格。
中國畫在符號上最鮮明的特征在筆墨,它源于以線造型的實踐方式,而“線”在客觀世界的物理環境中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對于線條的美,中國人有著獨特的審美視角和深層的哲學感悟,是最為純粹的形的抒寫。薛亮山水畫中出現的大量前人未見的程式或造型范式,卻在細節中處處流露出傳統脈絡或古人消息,在以線造型過程中有常理、得古法而能出新意、達性情。譬如薛亮畫太行山,山石結構明顯有李唐、劉松年等南宋人的某些特點,但在線條排列上更加整肅,渲淡層次上更為概括,設色程序上更為豐富,因而重組后的古人符號已悄然化合為帶有鮮明薛亮畫風特征的譜系化的藝術語言表達方式。而薛亮個人山水符號最根本的建構理念在于其對筆墨的獨到理解和精神研究。
在中國畫中,筆墨即可視為符號,程式則是綜合性的符號,它們都是抽象化的意象。我們在薛亮大量個性程式中可以不斷歸納整理出極為豐富的個人符號,這些一樹一石、一山一水的形態構成即可看到畫家的筆墨個性。所以筆墨也可作為抽象化的過程,它包含了想象、概括、簡化、提煉、升華等等因素,而同時程式又是一切抽象元素必須具備的條件,它起到規范、約束、平衡抽象因素的力量,也是劃定、構建本門類藝術語言符號內部秩序和外部形態的基本范式。簡言之,筆墨與程式都是中國畫必不可少的,單一的強調筆墨而忽視章法、造型、色彩等其它繪畫本體因素,必然把中國畫推向陳陳相因、空泛概念的僵化程式。反之,一味圖構程式的視覺新鮮感,主動喪失書寫性的筆墨符號則可能把中國畫引入另一種歧途和支流。所以薛亮也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符號要具備書寫性,不具備書寫性的畫就易做作,即為畫病。”
對于筆墨的認識,薛亮甚至有更為驚世的論斷:“筆墨形態千變萬化,用之不當則傷境。”單純從字面意思,此言必然會給人歧義和爭議,但結合薛亮的作品,實際上他以非凡的膽識實踐著中國畫追求以意境、神韻為本質的東方美學精神,以看似矯枉過正的論點點醒近世以來沉迷于玩弄筆墨趣味的“文人氣息”,力圖重建宋元山水那種遠逝的高華樸茂、沉雄博大的大氣象、大格局。因而薛亮的山水符號盡管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但它們是充滿東方智慧和民族傳統的邏輯秩序,一種充滿情感智慧的、文化積淀的、精神指向的,同時具備書寫性特質的符號系統。
天-鵝-170×170cm--薛-亮
(四)“引書入畫”的新解與新變
提及薛亮山水畫中的書寫性,必然要牽涉書法對薛亮畫風的影響。“以書入畫”是傳統命題,但在薛亮得到的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借鑒,更催生了其藝術觀和審美趣味的特立獨行。他認為在書法構成中注重一在筆法,二要講究構成美,這其中包括書法文字的造型與節奏。其中后者往往為一般畫家所忽視。書法從文字的象形會意到其后隸書、金文、魏碑、楷書是表現意識從萌醒到自覺的過程,而對筆墨的嫻熟駕馭使得書法集形式與內容于一體,實現情感表達的完滿自足。但畫家“以書入畫”的“尚意”觀念使得中國畫在“輕形”的路上走得更遠、更徹底、更極端,它把早期中國繪畫“以形寫神”傳統推向了文人畫“得意忘形”“逸筆草草”的新境。與只能徘徊于筆墨趣味的畫家有所不同的是,薛亮在書法的結體、章法以及造字的原則中悟出了中國畫審美節奏的內在形式—線的書寫性與符號的統一性。所以理解薛亮山水畫中的書寫性,應側重書法形式的構成與生發,把握繪畫語言符號的整體與純粹,而不計有筆筆來歷的筆墨守舊與古趣。
值得指出的是,薛亮追求的圖像或章法根植于我們民族傳統文化而非西方潮流。盡管當下西畫種種思潮對中國畫造成巨大沖擊和影響,但薛亮自己并不認為他受到多少西方因素的影響,反而與之保持距離。他曾言:“西方所謂的形式邏輯構成,拋掉構成精神指向是什么?而我在書法中讀到了東方構成概念與精神指向。”
綜上所述,薛亮的山水畫風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的、延展性的、富有學術意味的研究課題。其所展現出的學術價值遠遠大于人們的想象:薛亮筆下的山石云水負載深刻的傳統意識、歷史意蘊和多向性的時空關系,形成了觀者與畫家更為廣闊而神秘的心理空間和意象張力。這些具有鮮明薛亮個人標記的繪畫符號共同構成了既可直觀于縑楮的形象,又由此暗示出需觀者自行領悟的無形的景象:它們如鏡中水月、空靈飄渺,預留了觀者的無限遐思,實現了屬于這個時代又基于民族傳統的美學價值和藝術風尚。《莊子·天下篇》說:“古之人其備乎!……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此言講古之圣人應該具有把內外、本末、大小、精粗等本來對立的因素統一起來的能力,借用到繪畫上來無不可徹透辯證統一的藝術本質規律。真正的大畫家應該是創作精神要有堪比神明的高邁和統御力,而創作過程中又要以最勤勉的務實作風才能實現作品在技巧層面的“盡精微,致廣大”。薛亮是一位“極高明道中庸”的藝術家,他以哲人的思維見諸畫家之筆端,勤于藝而訥于言,在甘于靜寂淡泊的漫漫從藝之路中實現了“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的境界。因此,薛亮山水畫風是我們這個時代出現的而又超越這個時代的藝術形態,它為中國畫傳統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拓展理解傳統的空間,為傳統通向未來開辟出一條新路,在這條路上薛亮以自己的星星之火為后人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本文作者系江蘇省國畫院副研究員、傅抱石紀念館副館長、東南大學藝術學博士后)
薛亮
1956年2月生于江蘇省靖江市。現為江蘇省美術家協會顧問,江蘇省中國畫學會副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丶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江蘇省書畫院院長。第九屆江蘇省政協委員,第十屆江蘇省政協常委,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民盟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副會長,盟中央美術院副院長。獲首屆江蘇省委省政府紫金文化獎章。作品入選“第六屆中國藝術節國際中國畫大展”,第一、二、四屆“全國畫院雙年展中國畫展”。
責任編輯:邢志敏
文章來源:《畫界》2022年3月第二期
版面設計:湯煒
編輯:畫界 邢志敏